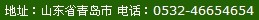|
胜日寻芳泗水滨,无边光景一时新。 等闲识得东风面,万紫千红总是春。 ——朱熹《春日》 朱熹的《春日》是一首清新自然的诗作,本来就惹人喜爱,自从收入童蒙读物《千家诗》后流布更广,几乎是妇孺皆知。由于它是七绝,形制短小,语言通俗,没有疑难字句,平时阅读时除了领略诗中描绘的景象美与蕴含的哲理之外,很少有人注意到它潜在的解读复杂性。年春夏之交受托编写《百科图说千家诗》,不时翻阅前贤时人著作,才意识到在诗意理解上的严重分歧。 作者译注《千家诗》,中华书局出版 从字面上看,这是一首游赏之作。诗人徜徉泗水河畔,感受到了春天节令一新、景象万千,内心充满喜悦,对春天生机的赞叹油然而生,是一首写景抒情佳篇。尤其是首句用赋的手法,点明时间、地点与行动意图,与写作技法中的“开门见山”吻合,活脱一种纪实手法。这种阅读感觉是如此强烈,以至于大部分解读者都将它理所当然地定性为游赏写景之作。从行文上看,前两句写景,后两句抒怀,触景生情,情景交融,为七绝常见的结构方式。一般情况下,人们自然地得出结论:这是一首游春诗,描写了诗人河边踏青所看到的万紫千红的景象。“这首诗是作者为赞美泗水滨的美好春景而写”(谢枋得、杨业荣编选、宋锡福注《千家诗》,广西人民出版社,,第3页),从视觉和触觉两个方面写出诗人的感受(谢枋得:《千家诗全鉴》,中国纺织出版社,,第页);由于传统诗歌写实性的凸显,它被分析为一幅白描手法绘出来的闹春图(谢枋得、王相等选编、王岩峻等注析《千家诗》,山西古籍出版社,,第3页;马清福:《千家诗》,春风文艺出版社,,第4页;刘克庄选编、李牧华注解《千家诗》,甘肃人民出版社,,第页)。 然而一细究文字,问题来了。从地理位置上看,泗水位于今山东省中部,源于泗水县东部陪尾山下,由趵突、响水、洗钵、红石四大泉汇流而成,与运河相通,因四源并发而名。出县境后吸纳了西沂水、险水、汴水等,成为淮河下游最大支流。历史上常把泗河与淮河并称为“淮泗”。朱熹生活的时代,泗水流域为金人占据,朱熹没有出使过金朝,如何能够在泗水游赏呢?如此看来,这首看似简单的写景诗绝非泗水春日景象的写照(缪钺:《宋诗鉴赏辞典》修订版,上海辞书出版社,,第页;李宗为:《千家诗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,第14页)。 分析之后发现,这竟然是一首抒写内心感受抒写心象的作品,一首哲理诗而非写景诗。朱熹用了泗水典故,传达作为一个理学家学习孔孟思想的感受。因为孔子曾经在洙水、泗水聚徒讲学,所以后世用作孔子与儒家的典故。比如魏晋时期阮侃在《答嵇康诗》(其一)中写道:“唐虞旷千载,三代不我并。洙泗久已往,微言谁为听。曾参易箦毙,仲由结其缨。”从来没有到过泗水的朱熹用看似写实其实是虚笔的手法,在小诗中通篇用比体,隐喻的手法,用探寻春天以及对春天的勃勃生机的感受来讲明一个道理:只要进了孔圣之门,懂得了儒家真谛,就能领略到无边生机。朱熹哲学思想的表达含蓄,果然瞒过了不少人,比如编选七言《千家诗》的王相,说它是“寻芳游春踏翠之意”(谢枋得、王相:《绘图千家诗注》,清刻本,齐鲁书社影印本,,第2页),但是依然为不少人领会。明朝关学领袖冯从吾给弟子讲这首诗时说:“既识得东风面,则万紫千红总是春;安往非学,安往得厌,安往非诲,安往得倦。”(冯从吾:《少墟集》卷二“语录”,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影印本)拿这首诗作为激励向学上进的教材,讲解的侧重点就不是自然风光的欣赏与春天的赞颂,而是一种进取精神与为学境界。 正是看到了诗中的别有用意,深刻领会其中的哲理蕴含,有人对于诗中出现的景象提出截然不同的见解。这首纯粹的说理诗,写的是春日,却没有春日景象的渲染与描写,出现却是“泗水”“东风”“春”等意象,对于春的赞叹也止于“无边光景”“新”“万紫千红”等几个并无新意、并不代表春天丽日特色的词语(魏晋:《未觉诗情与道妨——朱熹〈春日〉解析》,《名作欣赏》年3期)。如此看来,朱熹只是用比喻的手法、诗歌的形式,表达了朱熹彻悟圣人之道的欣喜。因为哲理意味的彰显而忽略诗中景象的呈现的倾向,显然在诗歌解读与文体感知上走偏了。既然诗中有几个意象,难道不能让人生发联想与想象吗?在赞美春天的词语中,“东风”“新”“无边光景”“万紫千红”,虽然是最常见词语,可是组合在一起,却最能显示春天的生机与活力。单从诗中呈现的景象来说,前两句概括性极强的语句,突出了春的生意盎然,“无边光景”从地域上说明广袤无边的大地气象一新,而这种新的景物呈现是瞬间产生的,“一时”的连缀,表明时间的迅捷,从力度上突现了春的生机。如果说第二句概括性强的话,那么三四句繁花盛开万紫千红景象,则显得具体可感,景象万千。而其实质,这种万紫千红景象是“一时新”的具体体现。朱熹用比喻的手法,写出自然万物一遇到“东风”即春风,便呈现出勃勃生机与无限活力。春天化育万物,是一种不经意的自然过程,虽然它的能量与结果让人惊叹不已。所以诗人朱熹用了一个“等闲”,举重若轻地表达了对于春天的无限赞美与敬意。 这不仅让人想起六朝大诗人谢灵运长诗《登池上楼》中写的“池塘生春草,园柳变鸣禽”。与谢灵运的诗歌相比较,谢诗“初景革绪风,新阳改故阴”的意思,朱熹用了“等闲识得东风面”写出景象变化之因。杜甫《春夜喜雨》中用“随风潜入夜,润物细无声”句,描写春雨滋润万物,默无声息,从动作发出者角度。此处,朱熹是从万物感受春天激荡的接受者角度着笔。在谢灵运、杜甫、朱熹那里,春被人格化为一种形象,它催发了春天的景象。中华民族是一个富于诗意的民族。先民们把四季节令的感知幻化为有生命活力的神,掌管春天的是句芒,或名句龙,是神话中的木神,主管树木的发芽生长。随着时代的变迁,人们心目中渐渐淡化了木神的观念,但是直至今天,潜意识中季节是一种生命体。最典型的是朱自清的名篇《春》,文章中春天的脚步让人期盼,洗耳恭听。“作诗本乎情景,孤不自成,两不相背”(谢榛:《四溟诗话》卷三,人民文学出版社,,第69页),中国诗歌艺术讲究的是生动形象,情景交融,朱熹《春日》的感染力与蕴含,正是依托于诗中意境的营就。诗人通过春的力量与生机,表达了自己的哲学思索与人生感悟。认为诗歌体现了悟道的喜悦自然不错,可是提出这是最切近诗歌原意的解释,否认是治学之道的诗作却是让人难以置信的。 然而问题似乎并不那么简单。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有许多叫作泗水的地方,如湖北咸宁、广东高州、广西凌云、河南南阳,尤其是朱熹祖籍江西婺源,也有条河流叫做泗水。生于福建的朱熹虽然大部分时间生活在福建,但一生中曾有三年时间逗留江西、浙江、湖南、安徽一带,尤其是曾两次返乡祭祖扫墓。有学者认为,《春日》中的泗水就是婺源的河流。朱熹“素耽山水之趣”(《康塘三瑞堂记》),喜“耕山钓水”(《建阳云谷书院记》),两次回到婺源,抽暇拨冗,他漫步泗水之滨,深情地欣赏一下家乡的光景,不是情中之事吗?作为诗人,把所见所思凝练成句,描画一下家乡的春日,不也是对故乡的一种纪念吗?(张顺清:《对几个与〈春日〉相关问题的辨析》,《现代语文》年第2期) 的确,朱熹一生两次回祖籍祭祖扫墓(束景南:《朱熹年谱长编》,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,第、页),一次是绍兴十九年()十二月至次年正月初二,中进士之后荣归故里,是冬日;一次是淳熙三年()四月二十日至六月上旬,四十六岁,夏日,还在家乡建屏山书屋,作为祭祖纪念。两次都不是所谓的“草木葳蕤、花团锦簇”的季节,与《春日》景象不符合。朱熹祭祖,无论是进士返乡还是第二次作为一位文化名人,在当地无疑是一件大事,尤其是第二次,两个多月时间内,他与故乡学者、文人往来频繁,不少人来问学讨教,他为家乡图书馆撰文,屏山书屋的建筑也使故乡人睹物思人。朱熹是儒学的集大成者,在中国乃至世界上尤其是东南亚影响深远,如果是在家乡写的诗歌,或者是写的是家乡的景象,却没有留下时人唱和的篇章,让人难以置信。尤其可疑的是,如果如诗歌描写的内容与当地景观有关,彰显地域文化的地方文献竟然没有收入,这是不可思议的事。 除了《春日》之外,在朱熹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》中,“泗水”作为地名出还现在《乞以泗水侯从祀先圣状》(卷二十)、《决汝汉排淮泗》(卷五十二)、《偶读谩记》(卷七十一)中,都是通常意义上淮泗的含义,与孔子、儒学有关,没有祖籍婺源河流的印记。综合上述,以为《春日》是写婺源景象的诗篇难以说服人心。 其实,用虚构的景象入诗,传达人生思索的手法,在朱熹诗中并不少见。如《观书有感》第一首: 半亩方塘一鉴开,天光云影共徘徊。 问渠那得清如许,为有源头活水来。 不看题目,仅从诗歌字面上看,似乎是写景诗,实际上诗以半亩方塘做比喻,抒发读书时茅塞顿开的喜悦,说明只有多读书,根植深厚,才能境界开阔。第二首也是如此: 昨夜江边春水生,艨艟巨舰一毛轻。 向来枉费推移力,此日中流自在行。 诗以泛舟做比喻,说明做事情一定要遵循客观规律,客观条件到达了,就会事半功倍,一气呵成;做学问也要厚积薄发,功到自然成。由于景象鲜明,人们不禁将题目改作《泛舟》,从而淡化蕴含的哲学意味,迎合自己纪实性阅读经验期待视野(如影响深远的《千家诗》通行本将题目改作《泛舟》)。 《春日》寓哲思于景象,二者融合无间,让人遐思万千。于是出现了折冲二者之间的调和。这种看似折中的解读方法是,首先确认这是一首描写春游的名篇,不仅形象地概括了春天明媚的景象,抒发了春游时的愉快心情,借春游阐发了只要敢于探索,就能认识自然,从而驾驭自然的真理。春游的经验,自然能够联想到读书和做学问(谭秉刚编著《千家诗》,湖南文艺出版社,,第3~4页)。其次,这是一首讲解治学心得的诗,朱熹没有去过泗水,然而诗歌以景语写理,生动流丽,即使做游春诗解读,亦颇可观(谷一然:《千家诗评注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,,第3页)。看似中和,却是一种诗歌理解的错误。《春日》与《观书有感》一样,是哲理诗,而并非写景诗。哲理诗并非只以道学气息浓郁的面貌出现,还有另外一种,以具体鲜活而感人的形象让人不知不觉中悟出写作意图,如春风化物、春雨滋润,无声无息,沁人心脾。 一首看似简单诗歌的解读,引发如此难以想象的分歧与争议,实在是始料未及的事,而解读诗歌涉及文体知识、篇章结构、文本互文性、地理、时政、写作者思想观念。古人说,“诗无达诂”(董仲舒《春秋繁露》卷三),一般意义上是说解读的多样性,即所谓的“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”。现代文学理论知识告诉我们,诗歌是诗人、世界、读者之间的互动构建,一首诗歌只有在读者那里才能得到落实、呈现意义,因而读者解读的重要性受到空前重视,读者制造了他在文本中看到的一切(斯坦利·费什:《读者反应批评:理论与实践》,文楚安译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)。形式主义者强调文本意义,指出文学作品是一个独立的存在,在文本的内部解释评论,排除作者生平、经历、写作意图的考量,甚至有人以为文本的意义有待于读者的误读而呈现(赵毅衡编《“新批评”文集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)。这些理论,为理解《春日》解读中出现的情形提供了借鉴。然而,中国诗歌的创作理念是“诗言志”(《诗经序》),从创作论上强调诗人的情志传达,在解读上形成了“以意逆志”“知人论世”(孟子《孟子·万章》)的文本、作者、世界相结合的综合评论模式。按照传统诗歌评论理论,尽管诗歌解读存在着多种可能性,但是依旧有一个正解,需要我们透过意义的丛林去寻觅。 选自《文史知识》年第10期 (统筹:启正;编辑:平安)赞赏 长按北京看白癜风好专科医院治愈白癜风需要多少钱
|
当前位置: 屏山县 >张立敏诗无达诂与正解以朱熹春日
时间:2017/11/14来源:本站原创作者:佚名
------分隔线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- 上一篇文章: 7月18日湖北恩施中国仙本那屏山峡谷
- 下一篇文章: 生活百科洗衣液瓶做成花盆,太漂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