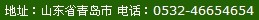|
山头角 山头角是一个地名。 曾经,在地图上,它被夹在福建日报和福建中医学院之间。 在我的地理概念里,龙峰新村、华屏路以及屏东河这一片区域,都是可以称为山头角的。如果从卫星地图上看,这里算是屏山的山脚下,我猜,山头角应该得名于此。 既然强调了曾经,就说明这个地名已经是过去时了。现在的福州地图上已经找不到这个山头角了,在城市飞速的发展建设中,它消失了,悄无声息。 遇见山头角时,我刚大学毕业,精力旺盛得恨不得天天熬夜。上夜班,最合适不过了。那一年的夏天,我到福州的华林路84号报到。对于这座城市的第一印象,真心没有太多感觉,也许没有特色就是福州最大的特色吧。在报社印刷厂夜班休息室混了几天后,我找到了落脚福州的第一个安顿点,师兄收留了我,他租住的房子,就是位于龙峰里山头角的龙峰新村。 从名字上看,龙峰新村应该是拆迁之后的安置小区。 小区里面有一座泰山庙,在一些特殊的日子里,我们常常被庙里的声音唤醒。庙里有一幅非常有价值的清代壁画,包括台湾府在内的福建八府十州的城隍,都在画中,为两岸罕见。若干年后,凭借这幅壁画,泰山庙成了福建省级历史文物保护单位。 新村充满着城乡结合部的气息,住在这里的几年,时不时会碰上本地居民在小区中办酒席,现垒大灶,鸡鸭鱼肉、海鲜贝类,不逊酒楼。偶尔,还会有露天电影,播放的是传统闽剧,娱神娱人。 新村非常适合租住,菜市场、修车摊、卤味摊、神仙庙,该有的都有,最重要的是,无论你在任何一个时段回来,都可以找到填饱肚子的小店,白天不用说,夜深了有沙县小吃,有几次等目录快到天亮,开包子店的莆田老板已经在忙碌了,油条已经炸好,散发出香味。 我至今记得,和山头角初次相遇时的情景。 一个夜班过后的凌晨,版面付印后,师兄带着我从印刷厂出来到宿舍区。我们走的是一条城中村的小路,路不长,但路灯昏暗,时明时灭,那条路崎岖不平,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。小巷两边都是村民的自建房,由住宅改建的不少店面已经租了出去,有的散发着暧昧的灯光,有的紧闭着门,警惕的老板审视着敲门的客人——其实就是家黑网吧,也有夜排挡和沙县小吃,在凌晨的夜里,抚慰肠胃空虚的夜归人。 “平时一个人的时候,还是走外面的大路,这里有点乱。”师兄说。然后,我听到了一堆可以刊登在都市报上的社会新闻,能吸引眼球的那种。 我生性胆小,在学校时,看见武术系大哥们在食堂和操场上叱咤风云,还以为江湖就是这样。现在想来,终究还是太嫩。 此后,我每日往返于山头角和报社之间,生活单调,或者说充实。当然,师兄的话肯定是要听的,夜班过后,我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从大路回宿舍。 这条大路就是华屏路。华屏路的一边是省直机关宿舍区,一边是屏东河。屏东河边上一排的小店,灯火辉煌,夏天的夜里,这里的灯火可以亮到早上。 在这里,我们经常会“偶遇”到报社各部门的同事,招呼之下,往往顺势就坐了下来,几杯啤酒下肚,几局棒子棒子鸡之后,革命同志之间的友谊迅速地得到了升华。那时候,我们都还年轻,头发浓密,尿酸不高,血脂不高,没有发胖的烦恼,这样的酒局来得恰到好处。 我一直觉得,每个城市都应该有这么一个地方,这里未必是这个城市最好的夜排档所在,卫生一般,菜也普通,啤酒可能还是买一送一的低档货。但这里却是媒体人最集中的地方,昼伏夜出的编辑记者们在这里激扬文字,挥斥方遒。 这种地方,在广州可能叫杨箕村,在福州,我觉得就是山头角。那是媒体人的深夜食堂,是安放躁动灵魂的所在。在山头角的小店里,我们一大群人,都见过凌晨四点的福州城。 现在想起来,屏东河边上那一排小店都留下过我们出没或者战斗的身影,不少店已经忘了名字,但流连在山头角的时光却永远不会忘记。 在报社食堂没有重建之前,木花“大酒店”是我最常去吃午饭的地方. 常去的原因自然是这里有招牌菜,木花的招牌就是扣肉,点三四块扣肉加上酸菜一炒,香极了,相当下饭。木花的饭也给得很实在,敞口的饭碗,装得冒尖的米饭,相当大气。店里没有菜单,要吃什么就在冰柜前现点,老板娘操着浓厚的福州腔,一边飞快落笔一边大声通知厨房做菜,爽快利落,雷厉风行,一荤一素一汤,吃得非常过瘾。 木花也做夜宵,不过我们去得较少,边上那家小炒还有传说中的寿宁店,我们去得相对多一点。媒体人都是夜猫子,一喝就到深夜,甚至到天亮。老板娘没那个耐心,时间差不多了,声音就不耐烦了,于是,这钱就让其他能熬夜的人赚了。 十几年前,还是纸媒的黄金时代,尽管大家都是戴着镣铐跳舞,而且一直如此,但我身边的同行们,不管身在党报还是都市报,我都能感受到他们身上的热情,那是一种在新闻理想的感召之下的激情。其实,我们大部分人都没想着要“铁肩担道义”,但有些事,遇见了,总不会不管,毕竟,血,总是热的。 水,越喝越寒,酒,越喝越暖,的确,酒是很好的载体。 在山头角的小店里,不管你是哪种气质,胆汁质还是多血质,甚至粘液质,在酒精的催化中,都会放荡形骸。 我们谈论传媒界的大大小小的掌故,甚至八卦;我们也会争论一些观点,不管先锋还是无聊。在这里,不论你是“白日放歌须纵酒”的中文系,还是“黑夜跳舞好揩油”的新闻系,都是一种从容的状态:不逃避,不放弃,三杯一小组打个通关是基本动作,至于吹瓶或者大碗上来,也不是没有过。更有豪气干云者,直接拿个桶,放在脚下,吐给你看。酒酣耳热时,也能听到谆谆教诲,“认真工作乃安身立命之本”,都是真心话。 也就是在山头角,你才发现平时那中规中矩、一派规矩面孔的同仁里,隐藏着那么多的“扫地僧”,他们才华横溢,胸怀天下,然而,装住他们的袋子实在太厚了,出不来。后来,我看了《肖申克的救赎》,才知道,其实,这就是体制化。 那一年,和我一同进报社的年轻人有十几个人,真是来自五湖四海。军训过后,分配岗位,新人往往都要在艰苦岗位走一趟,要么上夜班要么到记者站去。各分东西之后,偶尔小聚,也多是在山头角,毕竟那个时候,扣掉租房的钱,大多数人都是囊中羞涩。十多年后,十几个人真的各分东西,原本还想走一趟长乐金峰的想法,好像再也没有提起。 我的酒量就是这么练出来的。有那么一段时间,一种红标的雪津还是惠泉搞再来一瓶活动,喝了一箱再送一箱,也就是在山头角这样的小店才有。当然,代价也显而易见,很多人看我刚进报社时候的照片,再看看我,都会说,这完全就是两个人。是的,岁月的确是把杀猪刀。 深夜的华林路 后来,我们陆陆续续搬离,山头角也面临拆迁,我们渐渐转战各种字体的“鸭棚子”“红锦天”这些地方,有人继续坚持,有人退出江湖。 再后来,省直机关宿舍区成了屏东城,山头角的民房盖起了楼房,小店消失了,连同地名一起。成了回忆。 在山头角的岁月,其实不长,就像我们常抽的特醇红双喜,实在不经抽,深吸一口,就烧掉大半。这燃烧的就是我们的青春,吐出的烟雾好像回忆,很快消散,只留下烟灰点点,提示着曾经有过那么一段时光。 现在想来,我想,福州这座城市的特色,就像山头角,如同黄昏下市井中那一抹夕阳,多多少少能给外来人一点温暖。 END 图片 网络 饕餮行星 陈文波赞赏 人赞赏 长按北京正规的治疗白癜风医院重庆市治疗白癜风最好的医院
|
当前位置: 屏山县 >流年在消逝了的山头角,见过凌晨四点
时间:2018-8-24来源:本站原创作者:佚名
------分隔线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- 上一篇文章: 8旬老人还在路边卖李子,贫困县老农急求
- 下一篇文章: 没有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