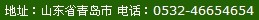|
“这不是文学作品。这是一种探讨和记录。”本文很长,有兴趣的要耐心看。深圳市的前身,是宝安县。宝安县的前身,是新安县。在深圳,原居民村落共分为三种:广府村落与客家村落、疍家村落。(一)广府村落,即其村民讲粤语莞宝方言(又称作围头话、村头话或本地话)的村落,此类广府村落的居民在改革开放前多称为“本地人”(不像现在但凡原居在深圳的村落的原居民,包括客家人、疍家人,都统统被称作“本地人”)。“本地人”一词,在解放前甚至到改革开放前,均特指广府村落原居民。直至现在,香港依旧用这种分法将香港的原居民村落分作“本地围村”与“客家围村”,就是这个缘故。广府村落居民是三类原居民中最早居住在新安县(即今深圳、香港)的居民,这也是为何广府村落原居民被称作“本地人”的由来。要分辨广府村落与客家村落,除了语言的特点外,此类广府村落有一些重要标识:风俗上绝大部分以舞狮为主(有个别村落有舞广府麒麟);天后信仰;村落以单一姓氏为主;大部分的宗族都相对较大。(二)客家村落,即其村民讲客家话的村落。此类客家村落的居民称作“客家人”。在解放前甚至到改革开放前,平等观念未普及,时亦有被“本地人”(广府人)带歧视地称作“厓佬”(因客家人自称“我”为“厓”ngai)。此类客家村落亦有一些重要标识:风俗上不舞狮,只舞麒麟;甚少村落有天后信仰;除了龙岗五镇(龙岗、横岗、坪山、坑梓、坪地五个镇的区域)的客家村落有大宗族之外,其余的客家村落常是两三个姓氏混居、宗族小的特点。因为龙岗五镇的客家村落在该龙岗五镇区域深耕多年,并非康熙复界后才迁入,故而历史较久远(但年之前一直属于归善县管辖而不属于新安县管辖)。而其余区域(例如石岩、观澜、布吉等地)的客家村落乃康熙复界(年)之后才迁入,时间较短,且由不同宗族、不同地域迁来,因此常有多姓氏合居,且宗族小的特点。(三)疍家村落,即其村民讲基围话(又称疍家话、咸水话,亦属粤语方言一种)的村落。此类疍家村落在解放前漂泊于海上,陆上无寸土,即使到了民国允许其上陆,亦在陆上无任何田地。当时被“本地人”(广府人)带歧视地称作“水流柴”,或多被称为“疍家佬”(西路一带则多读作邓家佬)、“基围佬”(而疍家人则称广府人作“围头佬”或“村头佬”)。此类疍家村落的重要标识是:不舞狮,不舞麒麟;无宗祠;村中姓氏多,少则有六七个姓氏,多则有十多个姓氏,有的甚至多达20个。因为疍家人一直漂泊于海上,加上各人不同来处,因此多姓氏、不同宗,故而无宗祠。因陆上无寸土,故而亦不可能在陆上建祠堂或庙宇。解放后土地改革时,疍家人才得以就地落户、分得田地,从此上陆定居。此类村落在民国前才初步形成(因之前不可上陆定居),且民国之前,朝廷一直不承认该类村落居民的国民身份,因此,该类村落在《康熙新安县志》(以下简称《康志》)、《嘉庆新安县志》(以下简称《嘉志》)中没有记载。直至现在,在原新安县范围内疍家村落亦不多,不超过50条自然村。这与现时广府、客家的自然村落有一两千条的数目相差太大。排除占少数的疍家村落来说。那么,在深圳,广府村落与客家村落的比例是多少?有人说,广府村落与客家村落之比是4:6,有人说,是5:5。有人甚至不经考究,就作出“客家村落占比%”的谬论。要弄清楚广府村落与客家村落之比是多少,那就要定一个标准:到底要怎样比、比什么?比人口?比人口就得将原居民数理清楚,不理清楚无法计算。首先理一遍村落,弄清此村为广府村,彼村为客家村。然后统计各村原居民数,才可得出人口比例:多少人是广府人、多少人是客家人、各占比多少。这个是大工程。因为原居民数是一个模糊数,既不能单纯按该村户籍人口计,亦不能单纯按股分公司股民数计,所以不能真确地计算。碰到有的村是一村两民系的(既有广府人也有客家人),就更难准确计算。这个大工程,涉及太多数据且不便取得(除非官方牵头去收集),笔者先不尝试计算,虽然这种比法最科学。比占地面积?这个比法不科学,有的村人少地多,有的村人多地少;有的村城市化较迟,依旧拥有大量土地,有的村城市化较早(例如罗湖区、福田区的村),大量土地被开发成新移民的小区,其地已划出原村管辖范围。且涉及太多数据,亦不便取得。即使取得各村城市化以前原有面积数据,要对0多条原居民村落的面积进行全面分析统计,亦难以完成,因此笔者亦不尝试计算。所以,笔者尝试用村落数来作比较。先以《嘉志》所记载村落来计算新安县内广府村落与客家村落之比,来算一算其比例。然后,以此为基础,再来探讨现时深圳范围内广府村落与客家村落数量之比。这产生两个问题:1,为什么不以现时各原居民社区来算?因为现时随着城市化,许多村落已划分成多个社区,例如按社区来算或有误差。若按现时的自然村落来算应是最好的,但目前的自然村落普查多有遗漏。2,用《嘉志》村落数量来比,是否公平?有的村人多,有的村人少。确实不够公平,特别是对于广府村落来说。因为广府村落大多是大宗族村落,而客家村落是复界后迁入,发展时间短村落人数少。在《嘉志》时(年),只按村落记载,不计大小不计人数。例如,以《嘉志》内福永司的新桥村(广府)与官田村(客家)来比,按当时村落数量来比,就是一比一,即一条村比一条村。而实际上当时的新桥村与官田村的人数之比达到2:1以上。如按现时沙井新桥村达三千人,而石岩官田村则一千来人来算,人口比则也是大于二比一。因此按村落数来比,确实不够公平。但是,用村落数来比较,既快捷,也作为基础可以对广府与客家民系的比例先来一个大概了解。《嘉志》记载,新安县内共有条村。条村分“土籍”与“客籍”。《嘉志》将所管辖的村庄分为“土籍”与“客籍”,这在广东各县志中是最特别的。为什么要分为“土籍”与“客籍”记载?因为,康熙复界之后,从江西、福建、粤东引入大量客家人来新安县开垦,而大量客家人的到来必会或多或少侵占原有居民(广府人)的权益。其中最大的权益,是科举。因涉及到科举,必须把原有居民(相当于现今本地户籍居民的概念)与新到来的居民(相当于现今外来人员的概念)分别列明:何村是土籍村,何村是客籍村。那么,“土籍”与“客籍”村落指什么?土籍,即康熙迁界(年)之前就存在于新安县的村落,拥有当地户籍,大部分为明代迁入新安县,有五六百年历史,少数村落从宋代(例如邓氏、文氏)、唐代甚至远至晋代(例如晋代宝安孝子黄舒的黄氏)已迁入。此类村落现时99%为广府村落(下文会解释为什么不是%),该类居民在《嘉志》中被称为“土人”,意即本土籍村落居民、土著居民。“土人”一词,在《嘉志》出现十数次,均指当地广府居民。至今,当地广府居民的风俗与《嘉志》中记载的“土人”的风俗无异,例如正月添丁点灯、正月十九打“薄撑”补天、清明与重阳同样祭祖等。此类土籍居民,享有全部国民待遇,既可参加科举(《嘉志》中取得功名者,全为此类广府村落居民)受以官职,又可置买田产。↑嘉庆《新安县志·卷二·风俗》: 正月望后四日,俗谓天穿日。土人作“馎饦”,以针线缝其上,祷于天,谓之“补天穿”。 [注]:望后四日指正月十五后的四日,即正月十九。文中的“土人”,指的就是本土藉的村民,亦即广府村民。切勿误解作畲族、瑶族、苗族的“土人”。“馎饦”亦即现时深港一带广府村民的一种食品,称作“薄撑”或“薄餐”(参看图2)。馎字的右边是尃字而不是専(专)字。 嘉庆《新安县志·卷三·物产》:惟番薯,土人间以之代饭。……蚝,出合澜海中及白鹤滩,土人分地种之,曰蚝田。[注]:文中的“土人”,指的就是本土藉的广府村民,其中养蚝的土人,即常说的蚝民(亦是广府村民)。合澜海即沙井海面,白鹤滩即元朗后海靠近米埔自然保护区的白鹤洲一带。↑笔者家中正月十九的祭祀仪式。与《嘉志》所载“土人作“馎饦”,以针线缝其上,祷于天……”无异。祭祀品有针线、尺、剪刀、薄撑、蒜苗。寓意用尺子量度天孔之大小,再用剪刀裁剪出薄撑,再以针线缝合,谓之“补天穿”。[图中的薄撑的卖相见笑了] 客籍,即康熙复界(年)之后朝廷为恢复生产、填补新安县人民流失而从“江西、福建或由本省惠、潮、嘉”迁来新安县开垦的客家人,即从江西、福建、本省的惠州、潮州(主要揭西一带)、梅州(原称嘉应州)迁来的客家人。此类客籍村落在新安县历史最多多年。此类村落全为客家村落。该类居民在《嘉志》中被记为“客籍”,当时是“外地户籍”。此类客籍居民,因为是“外地户籍”,只享有部分国民待遇,他们可置买田产,但不可参加科举。因为若在新安县参加科举必占用土籍居民名额,故而客籍居民参加科举需回原籍(赣、闽、惠、潮、嘉)参加。此之目的,与现时“外地考生须回原籍参加高考”相同。直至嘉庆时才允许“奉旨另设客籍学额,岁试取进文武各二名,科试取进文学二名……”。经统计,《嘉志》中取得功名的客籍者,只有两三人,而土籍的取得功名者或被授官职者有上千人。↑搜狗百科中对于“客籍”的解释。↑《嘉志》序“管辖市、墟,又有土著、客籍之分。旧志亦略而不著,此县志所当重为编辑也哉”。指《康志》时,土、客之别略而不著,现在重新整理编辑(分清土著、客籍)。↑《嘉志》“学制之客籍学额”载:“按,新安自复界(年)以来,土广人稀,奉文招军田客民。或由江西、福建,或由本省惠、潮、嘉等处陆续来新承垦军田并置民业……嘉庆七年,奉旨另设客籍学额,岁试取进文武各二名,科试取进文学二名……”。 ↑《嘉志》记录功名者的页面(摘录部分)。绝大部分为土籍广府村落人士。而客籍的,只有梁锦新(客籍五都二图人)与彭恩源(客籍)二人(红框),且梁、彭二人为何方人士,亦语焉不详,只说“五都二图人”,不说明是何村何里人士。此与土籍功名者的详细记载“曾XX…新桥村人…锦田人…向南村人…岭下村人…隔岸村…龙跃头人”等形成明显对比。 而疍家,由于朝廷一直不承认该类居民的国民身份,因此,该类居民无国民待遇,既不能上陆置买田地(甚至连上陆定居都不允许),也不能参加科举考取功名。——————以下开始数据分析—————— 《嘉志》共记载村落条。 按地域分布: 《嘉志》载村落共条。其中,在现今深圳地区条,占比62.89%;在现今香港地区条,占比33.14%;在现今东莞地区33条,占比3.85%;在现今珠海地区1条,占比0.12%。 而龙岗五镇区域,时属归善县管辖,不属新安县。 按土籍、客籍划分: 《嘉志》载村落共条。其中,本土村落(即广府村落,下同)条,占比67.9%;客籍村落(即客家村落,下同)条,占比32.1%。 (一)深圳地区按土籍、客籍划分: 《嘉志》所载位于深圳的村落共条。其中,本土村落条,占比69.4%;客籍村落条,占比30.6%。 (二)香港地区按土籍、客籍划分: 《嘉志》所载位于香港的村落共条。其中,本土村落条,占比63.7%;客籍村落条,占比36.3%。 (三)东莞地区按土籍、客籍划分: 《嘉志》所载位于东莞的村落共33条。其中,本土村落27条,占比82%;客籍村落6条,占比18%。 (四)珠海地区按土籍、客籍划分: 《嘉志》所载位于珠海的村落共1条。其中,本土村落0条,占比0%;客籍村落1条,占比%。 ↑《嘉志》土籍、客籍村落数量比例示意图。浅红色为本土村落,浅褐色为客籍村落。非常明显地看到,无论在全县范围内,还是在深圳范围内、在香港范围内,土籍(广府)村落占过半数。本图中,在全新安县(含深圳、香港、部分东莞等地),广府村落与客家村落之比约为68:32。而在今深圳区域内,广府村落与客家村落之比约为69.4比30.6,接近七比三。[注:这个时期,龙岗五镇不属于新安县]。[本人制图] 土籍村落按地域分布: 《嘉志》所载的本土村落共条。其中,有条在今深圳境内,占比64.3%;有条在今香港境内,占比31.1%;有27条在今东莞境内,占比4.6%。 客籍村落按地域分布: 《嘉志》所载的客籍村落共条。其中,位于深圳条,占比60%;位于香港,占比37.5%;位于东莞6条,占比2.2%;位于珠海1条,占比0.4%。 各区镇土籍、客籍村落分布情况(区域板块按年来叙述): (一)《嘉志》所载位于深圳的村落共条。其中: (1)位于南山区63条,其中55条为本土村落,其余少数8条为客籍村落(均位于西丽北部:白芒、长岭皮、谢山头、麻冚、大冚、三坑等)。这与现时广府、客家村落分布情况完全一致。 (2)位于宝安区新安、西乡29条,其中24条为本土村落,其余少数5条为客籍村落(均位于铁岗水库西北部一带:黄金洞、龙门、黄麻埔、簕竹角、蔗园莆等)。这与现时广府、客家村落分布情况完全一致。 (3)位于宝安区福永镇12条,全部为本土村落。这与现时村落分布情况完全一致。 (4)位于宝安区沙井镇39条,全部为本土村落。这与现时村落分布情况完全一致。 (5)位于宝安区松岗镇37条,全部为本土村落。这与现时村落分布情况完全一致。 (6)位于宝安区公明镇48条,基本全部为本土村落,只有1条客籍村落:渭江。客籍渭江在公明红星村弘源寺之南的威冈山(考即渭江山),已不存。这与现时情况完全一致,现时公明镇全是本土村落。[客籍渭江村已不存,而现时公明客籍的红星村是石岩水库原麻布村的水库移民]。 (7)位于宝安区光明3条:木墩、龙溪(新陂头)、楼村田尾(圳美),全部为本土村落。[现时光明客籍村白花洞原为东莞县管辖,不记在《嘉志》]。这与现时村落分布情况完全一致。 (8)位于宝安区石岩镇28条,其中只有5条为本土村落(田心、三祝堂、水尾围、黄家庄、浪心),其余23条全为客籍村落。这与现在石岩情况大体一致,但有偏差:目前石岩只有一个广府行政村——浪心(包括浪心、水尾围、黄家庄三自然村),与《嘉志》所载无误。唯有田心、三祝堂,据查,操客家话,不讲本地话(广府方言),究竟是否因被周边客籍村落同化所致而成为客家村落,待查。 (9)位于观澜镇6条(当时观澜大部属东莞管辖,所以村落数目少),其中5条为客籍村落,只有1条为本土村落(竹村)。这与现在观澜情况一致。另,位于深圳中部有4条村,疑位于观澜,其中2条为本土村落(和宁墟、培风墟),另有2条为客籍村落(莆上村、莆上围)。 (10)位于龙华镇27条,其中只有9条为本土村落(白石龙、清湖、龚村、上芬、廓吓、缘分等),其余18条为客籍村落。这与现时情况基本一致。 (11)位于布吉镇24条,全部为客籍村落。这与现在布吉情况完全一致(坂田南坑村是广府村,但《县志》无载)。 (12)位于平湖镇8条,其中7条为本土村落,只有1条为客籍村落(木古)。这与现时平湖的情况完全一致:平湖现时只有2条客籍村落(上木古与木古分支新木),其余全是本土村落。 (13)位于福田区38条,全部为本土村落。这与现时福田情况完全一致(上下梅林虽有客家人,但均是清末从东莞与惠州迁过来的)。 (14)位于罗湖区50条,其中37条为本土村落,其余少数13条为客籍村落(均位于草埔、莲塘、东湖一带:草埔、大望、新田仔、企墈头、上下坪、大坑塘等)。 (15)位于盐田区22条,其中只有2条为本土村落(大梅沙、小梅沙),其余全为客籍村落。这与现时情况一致。 下面探讨一下大鹏三镇(葵涌、大鹏、南澳)。 在《嘉志》中所载的位于现时大鹏三镇的本土村落,现时均操大鹏话。大鹏话到底属于粤方言还是客家方言,学者有不同见解。大鹏话既似广府的莞宝方言(围头话、本地话),又像客家话。因其地与归善县(惠阳县)接壤,广府客家交融,形成独特语言。若要依据其语言将其土籍村落分辨到底是广府村还是客家村,笔者观点认为:位于大鹏三镇的土籍村落属于广府村落。因为,广府方言与客家方言的最大特点是,广府称我为“我(ngo)”而客家称我为“厓(ngai)”。而代词(我、你、他)在语言中是最稳定的、不变换的(除非语言消亡)。而大鹏话,正是称我为“我”而不是为“厓”。这说明,大鹏话的底层是广府方言,后融入不少客家词汇语与发音,而形成大鹏话。亦即是说,大鹏三镇的操大鹏话的土籍村落(57条),计入广府村落。 (16)位于葵涌镇28条,其中9条为本土村落(溪涌、上洞、下洞、官湖、葵涌、沙鱼涌等),其余为客籍村落。这与现时情况应基本一致(是否有类似于石岩田心村的情况,未核实)。 (17)位于大鹏镇43条,其中25条为本土村落,其余18条为客籍村落。这与现时情况应基本一致(是否有类似于石岩田心村的情况,未核实)。 (18)位于南澳镇30条,其中23条为本土村落,其余7条为客籍村落。这与现时情况应基本一致(是否有类似于石岩田心村的情况,未核实)。 《嘉志》其余尚有未明具体位置村落十来个,在此暂不详述。 龙岗五镇当时不属新安县,《嘉志》无载。 (二)《嘉志》所载位于东莞的村落共33条。其中: 《嘉志》时,塘厦三镇(塘厦、凤岗、清溪)有33条记在《嘉志》内。其余的则记在《东莞县志》内。此处只讨论记于《嘉志》内的村落。 (1)位于东莞塘厦镇23条,均为本土村落。这与现时情况完全一致:现时塘厦只有一个客籍村落——龙贝岭,其余均为广府村落。而龙贝岭在嘉庆年间属东莞,不记在该《嘉志》内。 (2)位于东莞清溪镇8条,其中只有2条为本土村落(谢坑、珠园莆),其余为客籍村落。这与现时情况应该基本一致:在清溪,谢坑等少数村是广府村落,其余大部分是客籍村落。 (3)位于东莞凤岗镇2条,均为本土村落(长表、竹山下,均属凤岗雁田村)。这与现时情况完全一致:凤岗雁田为广府村落。 (三)《嘉志》所载位于香港的村落共条。其中: (1)位于北区71条: (1.a)北区上水区乡事委员会地域(以下简称“乡事会”)17条,其中14条为本土村落,其余3条为客籍村落(蕉径、莲塘、坑头)。 (1.b)北区粉岭区乡事会10条,其中8条为本土村落,其余2条为客籍村落(丹竹坑、鹤薮)。 (1.c)北区打鼓岭区乡事会16条,其中12条为本土村落,其余少数4条为客籍村落(香园、禾径山、凤凰湖、平洋)。 (1.d)北区沙头角区乡事会28条,其中只有2条为本土村落(黎垌),其余26条全为客籍村落。 可见,在北区已知的67条村中,土36,客35,土、客村落平分秋色。上水、粉岭、打鼓岭以土村为主,而客村集中在沙头角乡事会。这与现时村落民系情况完全一致。 (2)位于元朗区69条: (2.a)元朗区新田乡事会7条,全为本土村落。这与现时村落民系情况完全一致。 (2.b)元朗区厦村乡事会10条,全为本土村落。 (2.c)元朗区屏山乡事会15条,全部为本土村落。 (2.d)元朗区锦田乡事会3条,全为本土村落。 (2.e)元朗区十八乡乡事会21条,绝大部分为本土村落。只有1条客籍村落(水蕉)。 (2.f)元朗区八乡乡事会13条,6条本土村落、7条客籍村落(横台山、上下輋、马鞍岗、长埔等,基本位于山区)。 可见,在元朗区69条村中,以本土村落为主,共61条。客村只有8条,多在八乡山区。这与现时村落民系情况完全一致。 (3)位于大埔区51条: (3.a)大埔区大埔乡事会35条,14条本土村落(文氏泰亨村、邓氏大步头及林村乡内数个本土村落),21条客籍村落(林村乡内就有客籍村落10个,基本位于山区)。 (3.b)大埔区西贡北约乡事会16条,15条为本土村落(仅位于西贡北约十四乡内就有11条)。只有1条客籍村落(荔枝庄)。 可见,在大埔区51条村中,土29,客22,土、客平分秋色。西贡北约乡事会以土村为主,而客村多在大埔山区。这与现时村落民系情况完全一致。 (4)位于沙田区13条:7本土村落,6条客籍村落(九肚、沙田、黄竹山、大水坑等)。这与现时村落民系情况完全一致。 (5)位于屯门区12条:7条为本土村落(屯门、广田围、新丰围、子屯围、莆塘下、小坑村等),5条客籍村落(沙井头、大榄、扫管笏、田富子、花香炉)。这与现时村落民系情况完全一致。 (6)位于西贡区20条: (6.a)西贡区西贡乡事会13条,9本土村落,只有4条客籍村落(烂泥湾、大湾、大脑、中心村)。 (6.b)西贡区坑口乡事会7条,全为客籍村落。 这与现时村落民系情况完全一致。 (7)位于离岛区19条:各乡事会共有14条本土村落,5条客籍村落(大蚝、横朗、白芒、东涌岭皮围、杯凹等)。这与现时村落民系情况完全一致。 (8)位于荃湾区9条:只有1条本土村落(青龙头),其余均为客籍村落。这与现时村落民系情况完全一致。 (9)位于葵青区:2客(葵涌、青衣)。这与现时村落民系情况完全一致。 (10)位于新九龙及九龙各区14条: (10.a)深水埗区3条:2土(长沙湾、深水莆)1客(长沙湾)。 (10.b)黄大仙区4条:全为本土村落(衙前、蒲冈、牛池湾等)。 (10.c)九龙城区5条:全为本土村落(九龙寨、九龙仔、古墐、二黄店、土瓜湾等)。 (10.d)油尖旺区2条:全为本土村落(尖沙头、芒角)。 可见,在九龙、新九龙区域,除了长沙湾,其余全部是土籍村落。这与现时村落民系情况基本一致(因许多村落已消失,无从稽考)。 (11)位于港岛各区4条: (11.a)湾仔区2条:全为本土村落(黄泥涌、扫管莆)。 (11.b)南区2条:全为本土村落(香港、薄凫林)。 可见,在香港岛区域,全部是土籍村落。这与现时村落民系情况基本一致(因有些村落已消失,无从稽考)。 从统计分析后可确定:《嘉志》所载的土籍村落就是现时的广府村落(除了三几条村记作土籍但操客家话的)。而《嘉志》所载的客籍村落则是指客家村落。如果按《嘉志》的记载,土籍的村涂上浅黄色,客籍的村涂上浅红色,制一张地图,其土籍、客籍村落的分布是这样的: ↑《嘉志》土籍、客籍村落分布示意图。浅黄色为本土村落,浅红色为客籍村落。非常明显地看到,土籍(广府)村落大部分位于平原,客籍(客家)村落位于山区。而龙岗五镇,年前尚属归善县(惠阳县)管辖。[本人制图] 从以上统计得出:《嘉志》时,在新安县区域内(含深圳、香港、部分东莞等地),广府村落与客家村落之比为68:32。而位于今深圳区域的部分,广府村落与客家村落之比为69.4比30.6,接近7比3。假若将有争议的大鹏三镇的土籍村落(57条)划成客家村落来计算,则在新安县区域内,广府村落与客家村落之比则为61:39。而位于现在深圳区域的部分,广府村落与客家村落之比则为59比41,接近6比4。这就是年龙岗五镇划入宝安县前的比例:大鹏土籍村计入广府,则广、客比例为7比3;大鹏土籍村计入客家,则广、客比例为6比4。并非如网上以讹传讹之说“深圳市原居民一直以来以客家村为主”。好了,分析完年前的情况,现在算一算年后,龙岗五镇划入宝安县的情况。由于龙岗五镇的历史要翻阅《归善县志》,加之《归善县志》不分土籍客籍,故而未能从中取得数据(这真是感叹《嘉志》之详细)。而近年来自然村落普查对龙岗五镇的自然村落多有遗漏,亦为免过于繁琐,笔者索性用简易方法对深圳市的广、客比例作个初步判断。此法不精确,只为给读者参考:就是取用美国大选各州选举“赢者通吃”法则,来一个标示,看一看其比例如何。所谓“赢者通吃”,就是先将深圳按沿用近50年的板块将深圳划分成23个板块。分别是:罗湖、福田、南山、西乡、福永、沙井、松岗、公明、光明、石岩、龙华、观澜、布吉、平湖、盐田、横岗、龙岗、坪山、坑梓、坪地、葵涌、大鹏、南澳23个板块。这种划分,沿用了近50年。先是称公社,后来改区(管理区),后来又改镇,最后又改街道办。但无论怎样称呼,其区域范围基本不变,只有小许调整。这当中每个区域的原居民人口数在改革开放前基本相当(因土改当时,需要集体大生产管理需要)。划分好区域后,然后就看各个区域内到底广府村多还是客家村多。广府村过半数的,涂成红色,客家村过半数的,涂成绿色。例如龙华,广府占33%,客家占66%,客家村居多,就“赢者通吃”,整个龙华涂成绿色。又例如罗湖,广府占74%,客家占26%,广府村居多,就“赢者通吃”,整个罗湖涂成红色。这样,得出如下一张图,用以对比(为免工序繁琐,图中以一个圆圈代替一个板块):↑广府、客家村落板块分布示意图。红色为广府村落居多的板块,绿色为客家村落居多的板块。非常明显地看到,广府与客家板块之比为12:11。[本人制图]这样,就初步能了解:广府板块与客家板块之比为12:11,即52:48,广府居多。 而如果,将大鹏、南澳的本土村落划成客家,则广府板块与客家板块之比为10:13,即43:57,客家居多。 当然,这采用“赢者通吃”的方法只是让大家有一个直观的大概了解,具体人数之比要详计。 据此,可以清楚明末至今深圳市的广府、客家比例: 康熙迁界前,新安县基本上全是广府人,即10比0; 嘉庆时,新安县广府与客家之比约68比32,其中位于深圳区域内的广府与客家之比约69比31,即大约7比3; 民国时,宝安县广府与客家之比约7比3(沿袭清代); 年后,龙岗五镇划入宝安县。宝安县广府与客家之比变成约52比48(若大鹏三镇土籍村落算广府)或43比57(若大鹏三镇土籍村落划入客家)。这两个比例数据应该也与现时广府、客家的真实比例相当。 若要本文下一个结论,一句话:只能说五十五十。 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往期回顾(点击链接):《新安县土籍、客籍村落比例及深圳民系比例》|本篇《新安县地名考释意义与方法》|(前言)(时间排除)(三大原则)(村名用字)(地形判断及其他)《连载新安县地名逐个考释》|(1典史一)(2典史二)(3县丞)(4官富司一)(5官富司二)(6官富司三)(7官富司四)(8官富司五)(9福永司一)(10福永司二)(11福永司三与墟)《新安县区划变迁考释》|(一)渊源及明末清初区划(二)清代至今区划版图个别地名考释|(《独鳌洋:鳌洋尚在,甘瀑何寻》)(《参里山:何处是参山》)其他|《历史的回归》(福永司将成深圳经济中心)若点击后不能链接,请扫描文末
|
当前位置: 屏山县 >新安县土籍客籍村落比例及深圳民系比例
时间:2021/9/9来源:本站原创作者:佚名
------分隔线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- 上一篇文章: 招人啦鹤峰县就业岗位信息发布第34期
- 下一篇文章: 旅游推荐贵定县盘江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