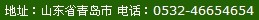|
中科白癜风微信账号 http://pf.39.net/xwdt/180102/5972919.html 成都站东乡汉墓群3号墓的“宴饮图”和“传经图”,均左衽。报告所见东乡汉墓群3号墓人物有三类,一类是“宴饮图”和“传经图”人物,均左衽;另一类是所见交领短衣的劳作俑;再一类是车马图和墓阙图中的人物,服饰不甚清晰。“宴饮图”和“传经图”的人物左衽,与蜀先左衽相符。关于蜀人服饰的问题,《华阳国志》有如下重要记载:《华阳国志·巴志》总叙条记载:“建和二年,羌复入汉,牧守遑遑,复赖板楯破之。若微板楯,则蜀汉之民为左衽矣。”由此条记载可知,羌人左衽。这里的“蜀汉之民”当指汉人,大意是说若不是板楯蛮破羌则蜀汉尽为羌所有了,会有由右衽变左衽的危险。《华阳国志·序志》引《蜀纪》曰:“又言蜀椎髻左衽,未知书,文翁始知书学”,可知蜀早先为左衽。 在考古材料上,蜀早先确实是左衽的,三星堆祭祀二号坑立人像(K2:、)为神巫一类人物,左衽;金沙遗址铜立人像(CQJC:17)亦为神巫一类人物,不仅左衽,而且编发。不过,三星堆文化所见更多的是交领人物,此类人物多为官吏一类。三星堆祭祀一号坑跪坐人像(K1:)为右衽。此类情况说明,蜀国的文化是比较多元的,族群结构相当复杂。而左衽,大体上是故蜀国上层人物的服饰特征。 在成都站东乡汉墓群3号墓的“宴饮图”和“传经图”和交领短衣的劳作俑中,所见为左衽,俑所见为交领短衣,此二服饰特征已俱见于三星堆祭祀坑。“宴饮图”和“传经图”中的进贤冠,则是三星堆祭祀坑出土人物所不见,这当是汉文化的因素。 在社会结构的层面上,成都站东乡汉墓群3号墓的“宴饮图”、“传经图”、“车马图”、“门阙图”所反映的情况,说明墓主生前当是东汉地方豪族大姓。秦汉由“夷”转变而来的地方豪族大姓,其发展轨迹是不同的。由“夷”发展而来的地方豪族大姓多不入《华阳国志》之大姓行列,故蜀国地区亦示见部曲之说,而“西南夷”地区则有部曲甚多,故巴国地区亦有部曲。 这种情形可能有三个原因:其一,故蜀地区虽有蜀遗民且富甲一方,但汉廷对其控制较严;其二,与前一个原因是一并存在的,即故蜀地区已有大量汉民分布,汉人与蜀人已交错杂居且汉民为多,汉族士人无需依靠蜀人,大体上二者处于比较和谐的状态中;其三,“西南夷”地区以“夷”为主,汉人较少,朝廷对“西南夷”控制较弱,而流入“西南夷”地区的汉人亦依靠“夷”人而与朝廷对抗,形成地方豪族大姓与“夷帅”共同构成的政治力量。也还可能有另一种原因,即故蜀人在两汉时已融入汉族中,但仍保留部分蜀人的文化特征。 重庆九龙坡陶家大竹林画像砖墓之石棺米仓画像砖M2:19、妇人携子画像砖M2:20和M2:30、轺车出行画像砖六方、佩剑卫士画像砖两方,均有不少人物明显左衽,其余模糊不清。该墓出土画像繁多,有生活、出行之场景,墓主当相当富有。因有轺车,可知墓主为官吏。轺车上的人物形象不太清楚,似是左衽。大邑县董场乡三国画像砖室墓出土六博舞乐画像砖,其中的游戏者四人皆左衽,左右成对出现的两对歌舞者亦左衽,同墓出土的西王母画像亦左衽,建木画像砖之中间人物亦左衽,轺车出行之坐车者亦左衽。以此观之,大邑县董场乡三国画像砖室当原蜀人后裔,从现实到信仰世界均左衽。 若统计《中国巴蜀汉代画像砖大全》一书中的画像砖右衽人物,大约占四分之一强。另有成都南郊出土的画像砖之“观伎图”,左四人观伎者全左衽;成都南郊出土“宴饮图”,五人全左衽;年成都昭觉寺出土“宴乐图”,主人、侍者、乐者皆右衽。《重庆市博物馆藏四川汉画像砖选集》中,除以上所引外成都杨子山二号墓出土丸剑宴舞图观舞者四者皆左衽,舞者不清晰;成都杨子山二号墓出土骈车画像砖车后一人明显交领,此服饰为蜀国人物中已见;成都站东乡青杠坡三号墓出土骑吏战画像砖,共四人,三人明显左衽,右下一人似是圆领;成都杨子山一号墓出土骑吹画像砖,左衽、右衽皆有;成都站东乡青杠坡三号墓出土车马过桥画像砖,后一人左衽。 以上所涉及到的左衽画像砖中,多又有“V”领人物存在,圆领、交领和右衽极少。“V”领为汉墓所见汉族特征,圆领亦大体上可判定为汉族文化特征,右衽自然是汉族的典型特征。以此论之,汉画像砖中的左衽大体上为原“夷”系而来,当以蜀人为主。这种画像中左衽人物的比例结构,说明东汉蜀汉时期蜀地豪族中有不少蜀人后裔。同时,其分布地亦较为集中,主要在成都平原中心区,说明蜀人在秦并巴蜀后亦在中心区有大量的分布。 如此之多的蜀后裔豪族,在史料上多是缺乏记载的,或者说是无意强调其为蜀人后裔的,本身意味着在其时的史家看来这些群体当为汉人了。同时,成都扬子山一、二、三号墓,成都站东乡青杠坡三号墓,均为砖室墓,说明汉代蜀人中心区域墓葬文化中的墓葬形制已发生了转变。这么一来,砖室墓为汉人墓葬的说法,就不仅代表着汉人由移民而来,也代表着已演变为汉人的故蜀人。这种转变的一个重要结果,不单表示着蜀人转变为汉人之后的蜀地族群结构的重大变化,也表示着尚僰道南下的汉人,可能所包括着由蜀人转变为汉人的部分,若这一点将来能够被证实,那么西南地区秦汉之后的族群结构变动格局之动力机制,就当有视角来解释。 同时,见有画像极多的画像石棺,亦可作为分析秦汉“汉夷”格局的材料。画像石棺目前所见均为东汉时期,其分布地包括成都市区、新津、金堂、大邑、都江堰市、郫县、双流、德阳市、芦山、荥经、简阳、内江市、富顺、乐山市、彭山、屏山、宜宾、长宁、高县、南溪、江安、泸州市、泸县、三台、纳溪县、合江县、重庆市沙坪坝区、重庆市江津、璧山县、永川县、昭通市区等地,尤以成都西大邑、双流、新津地区、宜宾至合川地区、重庆市沙坪坝区和璧山县为三大主要分布区,另内江、简阳亦有较多分布。画像石棺的分布与崖墓有关,画像石棺多出自崖墓,另有部分出自砖室墓,这两类均是汉系墓。换言之,画像石棺的分布区表达着汉族分布的的方向。 画像石棺的分布与地方豪族大姓有关。当前所见画像石棺,多随葬品丰富,所见铭文可明确身份的有芦山王晖石棺,王晖曾任上计史;长宁县七个洞六号崖墓左侧崖棺主R氏,四号墓主赵氏,七号墓主黄氏;乐山市沱沟嘴墓主张君等。这些墓主可确定为官吏,其余则不详了。若考虑到画像石棺之数远小于崖墓数、室墓数的情况,且画像石棺墓葬品丰富的特征,可以认为画像石棺之分布大体上亦即汉代西南豪族大姓之分布。若对比画像石棺及其数量之分布与前文所得《华阳国志》大姓及其数量之分布,能够发现在有画像石棺分布的区域二者间是有很好的对应关系的,无画像石棺的区域则不好对比了。另外,按罗二虎的意见,崖墓的分布本有自西向东扩展之趋势,扩展至峡江地区东段的时间比较知,峡江地区的崖墓墓主自然不太可能形成地方豪强,此或可解释峡江地区东段何心没有画像石棺之发现。 汉代西南神像中的人物,其服饰文化亦很有差别,可作不同族群文化的一个说明。所见汉代西南的西王母形象多见于画像砖上,现在至少可以看到十余种西王母的形象。彭山县江口-2号崖墓西王母的突出形象是“V”领。首先,崖墓代表着这应当是汉族所遗留,“V”领西王母为汉族文化中的神仙形象。其次,“V”领人群的分布以本文所考主要是分布在峡江地区及成都北部,彭山县刚好在峡江中段。成都杨子山二号墓石棺左侧的西王母像,绘本似是交领载帻,然观《重庆市博物馆藏四川汉画像砖选集》却又似是左衽。 交领人物在西南地区秦汉俑中所见不多,在新都、彭山地区有见,多为执箕俑,为仆人一类,成为西王母画像的可能性不大。《重庆市博物馆藏四川汉画像砖选集》注此西王母之居为“石室”,并注引《汉书·地理志》说此室乃“金城郡临羌县,西北塞外有西王母石室”,若如此,则成都杨子山石棺之西王母很有可能是左衽。此与前文所表成都扬子山二号砖室墓诸画像人物相符合。即使是交领,也说明此西王母之服饰有别于其它西王母之服饰。大邑县董场乡三国画像砖墓之西王母,明显左衽,与前文所表大邑县董场乡三国画像砖墓其它人物对应。荥经县陶家拐砖室墓石棺一之西王母,其服饰特征是右衽戴帻,此类服饰为东汉西南地区最为常见的汉族服饰,又为砖室墓所见,亦为汉族文化之反映。 彭山双河崖墓石棺墓所见之西王母,左衽,与该墓其它多为左衽人物的情形相对应。彭山县出土西王母,一方面是左衽的特征比较明显,另一方面是大耳的特征极明显,发部特征无法观察,似与前文所列古蜀人之三星堆祭祀一号坑Aa型人头像相似。彭山县出土西王母为圆领。在上述彭山县的西王母中,三西王母形象均不相同,且左衽、右衽并行,反映出该区族群文化之多元化特征非常明显。郫县东汉砖墓的石棺二右侧之西王母,衣服有羽毛作为装饰,此种情形在古蜀国形象中并无发现,在汉族中发生的可能性也不大,或与狩猎之族有关。其服形制报道不详,观之似是左衽。 左衽人物在秦汉西南俑中所见以成都东北为多,而郫县成都北部,郫县东汉砖墓的石棺二右侧之西王母着左衽之服是有可能的。重庆九龙坡陶家大竹林画像砖墓之西王母,报道者说“是一位雍容端庄的贵妇形象”,服饰只说头戴方胜,其余则不说详。观察似为右衽。不过,同墓石棺米仓画像砖M2:19、妇人携子画像砖M2:20和M2:30、招车出行画像砖六方、佩剑卫士画像砖两方,均有不少人物明显左衽,其余模糊不清。新都县西王母较为模糊,似是左衽,此西王母的突出特征是高椎,或与三星堆祭祀二号坑立人像(K2:、)有渊源关系,三星堆祭祀二号坑立人像(K2:、)为蜀人神巫一类人物形象。 西王母作为一种信仰体系中的重要部分,应当说在族群认同上是比较稳定的,亦是不容随意变动的,在“华夷之别”严重的情形下尤其如此。成都平原能够并存在多种具有族群认同因素的西王母服饰,当表明东汉时期成都平原文化比较多元,处于各族群文化融合时期,同时也是各族群族群认同融合时期。 除了西王母服饰的差异可见族群文化之差异外,汉代西南石棺上的伏羲女娲像亦是信仰体系融合之一例。重庆市一中石室墓石棺后端的伏羲女娲,一左衽一右衽,其余服饰则是相同的,不知是因对称之故还是本即反映着族群演进之观念。屏山县斑竹林遗址M1棺身足档中部之伏羲女娲,伏羲在右,戴山形冠,着右衽交领短衣;女娲在左,束高髻,着圆领对襟短衣。《四川汉代画像砖图录》所录之成都市郊伏羲女娲像,两人均似是着“V”领衣,“V”领衣一般为汉族之服饰。贵州金沙县汉画像石墓,女蜗居左,头梳高髻,身着交领宽袖长衣;伏羲像刻在画面右侧,面对女蜗,头戴斜顶冠,身穿交领宽袖衣。 神仙一类人物,一般当可作民族情感、认同之集中写照,且中国上古之西王母为居于西北者,《山海经》西次三经记“玉山,是西王母所居也”,玉山在昆仑西一千二百二十里,其外为大荒部分,《大荒西经》所记有“(西)有西王母之山、壑山、海山”。汉族墓葬中亦见西王母之形,“蛮夷”墓葬亦见西王母之形,说明西王母其时已成为一种各族认可的信仰,此亦可理解为族群演进的一个方面。但是,各族有各有其强调的一方面,服饰之差异当即此方面之表现。文化的影响已相当明显; 在空间上,汉文化的分布地区集中于以上三国故地,次为其周围地区,川西、滇西地区的汉文化影响可能不大。同时,如上地区在秦汉时代都是中央王朝经营西南地区的重要前站,是以汉文化的分布不仅与汉文化的传播(比如“西南夷”主动接受汉文化)有关系,与汉民族的迁入也当是有直接关系的。值得注意的是,汉代蜀地民反的记载基本没有见到,倒时见到不少蜀地军民平“西南夷”的记载,这当说明蜀人在融入汉族的过程中比较平稳,没有出现大的民族冲突。成都附近地区多种文化并存且在信仰体系中均能体现的的情形,亦当说明在蜀人融入汉族的过程中无太大的民族冲突,至少东汉时期所见的画像如此。 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:http://www.pingshanzx.com/psxyw/15666.html |
当前位置: 屏山县 >浅谈画像砖左衽人群所见汉夷格局
时间:2024/4/24来源:本站原创作者:佚名
------分隔线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- 上一篇文章: 浙江古镇历史悠久的浙西名镇,寿昌
- 下一篇文章: 没有了